阅读:0
听报道

由旅俄作家、翻译家孙越重新翻译的伊萨克·巴别尔的战争小说《骑兵军》最近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6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新译本首发式上,83岁的学者、翻译家蓝英年与孙越共同回忆了这部经典作品被译介的一些往事。
1987年,孙越开始翻译《骑兵军》。1992年,孙译《骑兵军》成为第一个汉语译本出版。
此后,孙越曾在苏联、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生活多年。2008年,他因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而获得俄罗斯皇家协会授予的圣尼古拉金质勋章。20多年后,孙越重新翻译此书,他称“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
近日,就孙越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及译作,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他。
巴别尔作品,在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
法治周末:1992年,你曾翻译出版巴别尔的《骑兵军》,能否谈谈你当时翻译的情况?
孙越:1982年,我的文学导师、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那时候,中国的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那时,我读书的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和俄文原版《骑兵军》,所以,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骑兵军》的情节。对我而言,这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
1986年,我第一次读到《骑兵军》原文。我记得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发现了《骑兵军》原文。它是一部复印件,而且肯定不是1950年代苏联再版的《骑兵军》,而是苏俄1920年代初版的。
1980年代中期,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准备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的小说。这是苏联自1950年代中期后,又一次重印巴别尔的作品。看来,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
也是在1986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所评选出的世界100位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翌年,我开始动笔翻译巴别尔的作品。1989年全书脱稿,1992年,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推荐,《骑兵军》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法治周末:巴别尔此著有多个译本在国内出版,其中包括傅仲选和戴骢两位先生的译本,书名都是《红色骑兵军》。你觉得自己最初翻译的这个版本跟他们的相比如何?现在的新译本又有什么不同?
孙越:我30岁以前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巴别尔出生、成长和死去的那些城市,如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以及莫斯科,所以,我不可能读懂他的书,译文亦幼稚可笑。20年后,我旅俄归来,巴别尔的形象才逐渐在我笔下变得清晰和明朗,他本人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才逐渐丰满和鲜活,栩栩如生地朝我走来。
如今,我有机会再译巴别尔,并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从而让新版更鲜活、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
法治周末:有这样一个实地采访和考察作为基础,此次翻译你是否感到更接近巴别尔的原著?
孙越:难以完全实现原著的一些韵味。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有,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
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
《骑兵军》源于我自童年与生俱来的恐惧感
法治周末:在巴别尔的人生经历中,神秘而吸引人一点的莫过于他的“契卡”(苏俄秘密间谍机构的前身)身份。他当初参加契卡的动机是怎样的?
孙越:年轻的巴别尔投身革命,他被接纳为红军“契卡”成员。巴别尔成为红军特工后,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洞悉俄国发生的一切: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爱情与性”。
巴别尔参加了“契卡”所有活动。他从新政权身上,窥见到愚昧、冷酷、残暴、肮脏和幻灭,于是,他开始如实地记录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巴别尔说,他在写作时,产生了幻觉:死亡如洪水猛兽,狂暴迅猛而至,他和芸芸众生,面对死亡,无路可逃,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
法治周末:《骑兵军》的创作主要基于巴别尔参加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军,当时他在这支部队的情况如何?
孙越:巴别尔于1920年加入布琼尼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他是该军参谋部主办的《红色骑兵报》的随军记者,他随部队在乌克兰西部与波兰军队作战。他亲眼目睹了杀戮和死亡,对他而言,骑兵军每一场战斗都是血与火的洗礼,死亡时刻在他内心引发剧烈骚动和恐怖。
那段时间,巴别尔除了写日记之外,还给骑兵军战地报社撰稿以及给各级指挥部誊写公文。所有这些文字,后来均成为巴别尔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有些则直接写入短篇体长篇小说《骑兵军》中。
法治周末: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骑兵军》如何得以发表?巴别尔的作品并没有高唱赞歌,那么他的作品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孙越:1923年至1926年期间,《骑兵军》部分篇章已在一些报刊杂志发表,引起文学界的关注。1926年《骑兵军》全书首发,巴别尔让文学界刮目相看,他作为横空出世的苏俄年轻作家,很快成为文坛焦点。
红色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对《骑兵军》强烈反感,布琼尼认为巴别尔的小说诋毁了红军骑兵,他愤怒之极,威胁要像剁白菜那样刀劈巴别尔。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是: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有高尔基出面保护,才使巴别尔免于政治灾难。
苏联解体之后,历史学家发现了巴别尔1939年的被捕审讯记录,他辩称:“《骑兵军》一书对我而言,不过源于我自童年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它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无关,但是其中确实渲染了国内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主义和色情主义……”虽仅寥寥数语,足见巴别尔当时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
法治周末:当时的社会环境应该说比较残酷,巴别尔是怎样认识和判断的?这如何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因间谍罪最后被判死刑,这是否是事实真相?
孙越:在巴别尔眼中,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叶若夫,在苏联1930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国家的“三套马车”。他们三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巴别尔便想起俄国画家沃兹涅佐夫的那幅著名油画《三勇士》。
因此,巴别尔开始悄悄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身边的人只隐隐听说,那是一部反间侦探作品,巴别尔甚至连家人都不点破小说的内容。其实,早就有人推测,小说的主人公可能是叶若夫。巴别尔曾对友人说,小说的名字是《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
1939年,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巴别尔,终于被从别列捷尔吉诺作家村带走,成了出卖祖国的嫌疑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巴别尔的记录。巴别尔在法庭上说,他在1930年代的最后几年,一直埋头撰写新书,并在1938年底完成了书稿,根本没有时间和经历从事间谍行为。最后,他还请求法庭给他时间,让他将新书写完。
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苏联老作家伊斯坎德尔告诉我说,巴别尔原本可以避开牢狱之灾,更不必惨遭死刑。但他为了他的写作,用生命去索取了那个时代的秘密。
作家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
法治周末:就同时代作家的作品看,《骑兵军》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越:《骑兵军》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20世纪人类的灾难。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38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
巴别尔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
《骑兵军》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相比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所写的《毁灭》,《骑兵军》的文学成就要远远高于它。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
法治周末: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观念,我们才能在《骑兵军》中读到《一封家书》这样的作品。这篇小说令人在平静的叙述中感受到很深的震撼,描绘出革命时代的真实面貌。
孙越:《一封家信》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直击心灵。小说描写父杀子、子弑父的过程。在小说中的男孩笔下,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却对此见怪不怪。但故事的精彩之处,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在小男孩心中,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
男孩哥哥的价值观很特殊,他觉得兄弟谢苗·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理由“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库尔久科夫深信,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新政权献身,未来要啥有啥,所以,谁碍了他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亲爹老子也不例外。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貌似怪诞,却非常合理。
《一封家信》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在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外省照相馆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
这既是对库尔久科夫家两兄弟形象的描述,也是为战争参与者存照:他们四肢发达,不学无术,却勇猛愚忠,亦擅以革命名义滥施暴力。这条特性主线,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被赋予道德感。
法治周末:战争是残酷的,人性与战争的搏击也是激烈的。
孙越:是的。在《骑兵军》中《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主人公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但他对此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
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
《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此举,他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
法治周末:通过这一些,你觉得巴别尔的《骑兵军》想告诉我们什么?
孙越: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兵军》告诉我们,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不仅使俄罗斯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那么,未来到底在哪里?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而他,也确实回答过了,只不过不是用小说,而是用他的生命。(法治周末记者 宋学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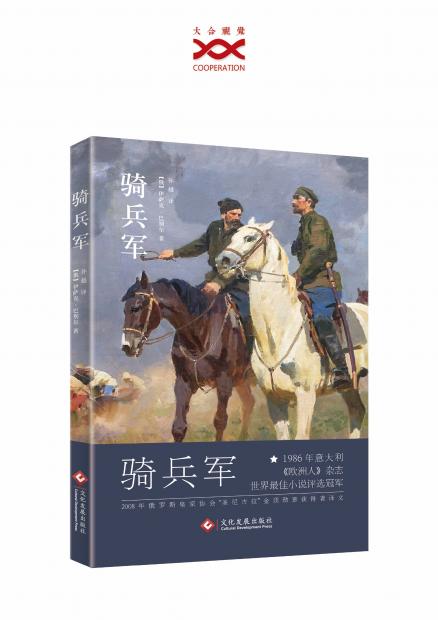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